新兵家信
■王 宁
那是20余年前的初冬时节,我们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离开了沂蒙大地的怀抱,毅然踏上了向西、再向西的征途。历经4天4夜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坐落在天山北麓的军营。
此刻,新疆已迎来了漫长的冬季,纷纷扬扬的大雪为天山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即便在严寒的笼罩下,玛纳斯河依旧奔腾不息,河水撞击着河岸,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声响。
当时,营区里仅有一部对外联络的电话,2000多人需排队等候使用。因此,书信几乎成了我们这些新兵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新训开始前,班长便递来一叠信封,让我们给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他还告诉大家,义务兵寄信免邮费。望着信封上那鲜红的三角邮戳,我心中涌起了难以言表的欢喜与荣耀。
当天晚上,全班人员坐在小板凳上,伏在床铺边,铺开信纸奋笔疾书。思绪顺着笔尖流淌,我把初到军营和旅途上的见闻和感受都写了出来。信中流露着我对家人的惦念,更流露着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一晚上下来,每个新兵班里都写出了比屋外积雪还要高的厚厚一摞信。
翌日,文书将这沉甸甸的思念抱走,而我便开始了漫长的期盼。我时常在脑海中描绘着父母收到信后的喜悦神情,以及他们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细读家书的温馨场景。
黄昏时分,我经常会伸长脖子、踮起脚尖,遥望连部的方向。终于有一天,文书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出现了。大家蜂拥而上,争相领取自己的家书。收到信的新兵们个个笑逐颜开,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躲到一旁细细品读。这些温暖的家书,为新兵连那酸甜苦辣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亲情的色彩。而那些尚未收到信的新兵,则眉头紧锁,心中充满了失落与焦虑。
“班长,我的信怎么还没有到啊?”我一次次地向文书追问。他总是打趣道:“干脆在你身上也盖个三角邮戳,把你寄回家去算了。”我则坚定地回答:“那可不行!我立志要在军营里闯出一片天地呢。”
经过好多个日夜的翘首期盼,终于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迎来了那封珍贵的家书。双手捧着这封穿越千山万水的书信,我感觉它沉甸甸的。我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抽出信纸,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有时,我会反复翻阅父母的回信,仔细揣摩其中的每一个字句,直到深刻领悟到家中所传递的每一条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的味道。倘若有幸能一次收到数封家书,那种喜悦与激动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新兵们所写的信虽篇幅有限,但情感却深沉而绵长。在与家人的通信中,我总是习惯性地报喜不报忧。然而有一次,在战术训练过程中,我的右手不慎碰到了戈壁滩上的鹅卵石,导致整个指甲盖被掀起,鲜血淋漓。在团卫生队接受包扎治疗后,我一个多月都无法洗衣、洗澡,甚至连写字都变得很困难。在回复家信时,我的字迹变得歪歪扭扭,父母一眼便看出了异常并来信询问原因。面对他们的关切与担忧,我只得如实相告。所幸的是,当他们收到回信时已是1个多月之后。那时我的手伤已经康复,新指甲也慢慢长出,我得以重新投入正常的训练之中。
对于那些已有恋人相伴的新兵来说,女朋友的来信无疑成了战友间公开的秘密。大伙儿常常聚在一起分享这些充满甜蜜与温馨的信件,甚至连一向稳重老成的班长也忍不住凑热闹。偷偷瞄上几眼那清秀的笔迹后,他严肃的脸庞上也会绽放出难得的笑容。班长知道我在入伍前曾发表过不少文章而且是一名党员,因此他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与我交流。有一次,他连续好几天都显得闷闷不乐,原来是他家中介绍的对象给他来信了。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对于如何回信感到十分苦恼。在苦思冥想了两三天后,他终于向我求助,希望我能帮他给对象回一封信。尽管我内心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为了写好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认真研究了那位姑娘写给班长的信,并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指导班长撰写了一封长达5页纸的回信。
在书信来往了3次之后,终于在一个周末,班长的对象不远千里从甘肃老家赶来部队探望他了。在那位姑娘来队的一个星期里,班长每天都乐呵呵的,仿佛吃了蜜一般甜美。自那以后,他对我更是刮目相看,并时常鼓励我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到了年底,班长复员回家不久后,便与那位姑娘喜结良缘了。
如今回想起来,新兵时期的每一封信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我们对家人的深切思念、对军旅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书信不仅是联络情感的纽带,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慰藉。
作者:王 宁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责任编辑:唐诗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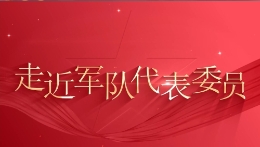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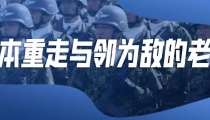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