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御史监察”看官员监督的独立性
古代“御史”的法律地位自秦汉迄至明清时期,大体上呈现出一种逐渐上升的态势。在古代政制结构没有出现较大变动的情况下,这种态势既反映了朝廷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控制的愈益重视,同时也透射出古代统治者意识到固有制度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治国需求,意图通过“制度微调”来弥合两者,从而维持政制的稳定及正常运作。
在历代王朝中,除了从制度层面对御史监察作出明确规定之外,御史监察在制度运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所谓“御史监察”,就是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吏进行监察,遇有违法之情案即予弹劾,通常再由朝廷授命法司专审或者会审,定其罪罚。然而,古代御史监察的运作状况及其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呢?仅以唐代正史记载为例,筛选统计近40起案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回答和描述。
其一,从弹劾者与被弹劾者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弹劾者或者负有监察职责者主要包括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基本涵盖了唐代御史台中直接享有独立监察权的全部核心组成官员。换句话说,在御史台的构成中,无论品秩高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虚职或闲职,均属负有监察职责的实职官员。另一方面,被弹劾者则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既有省部官员,也有监寺官员,还有州府官员,甚至还包括军事官员和监察官员。同时,涉案官员的品秩从正八品到正二品不等,既有低品级的大理丞、监察御史,也有高品级的中书令、尚书仆射及诸部尚书,足见御史监察弹劾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
其二,从御史监察弹劾的违法行为来看,涉及诸多方面,重者如“与妖人交结,谋不轨”,轻者如“违诏进奉”等。如果根据《唐律疏议》的体例标准,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谋危社稷,属于“十恶”重罪,有1件;违反职制,如贪赃纳贿、违失仪制等,有32件;斗讼,如主杀奴婢等,有1件;杂犯,如侵占巷街、误毁稼穑等,有8件。据此,在御史监察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中,虽然也有“十恶”重罪、斗讼、杂犯等类型,但更多的仍然是官员违反职制的犯罪,约占总数的76.2%,或许这也正是古代御史监察案件的一个典型特征。
其三,从御史监察弹劾的法律效果来看,在唐史记载有处置结果的37件案例中,有3件明确得到皇帝诏书的原宥;有2件虽然以特殊原因而免罪,但仍然被处以“贬官”和“征赃”;在其余的案例中,被弹劾的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处罚类型具体包括:死刑、流刑、抵罪、免官、贬官、夺阶、罚俸、征赃等。如果将“左授”“罢为”“左迁”“下除”等都视同“贬官”的话,那么,在统计受到弹劾的官员中,有23位被“贬官”,在承担罪责的案例中约占62.2%;如果再加上被“免官”“夺阶”“罚俸”“征赃”等案例,那么,涉案官员受到处罚的所占比例就达到83.8%。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御史监察弹劾的案件中,直接适用法定正刑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是对涉案官员适用诸如贬官、免官等从刑。
综上所述,在御史监察弹劾的案件中,虽然有制度上御史与被弹劾官员之间的品秩逆差形成的可能阻碍,但在实践中,御史经由弹劾而展开的监察是卓有成效的。
虽然在御史监察的实践中,时常会发生以皇帝宠信或者权臣势重等原因而赦免被弹劾官员的特殊情况,但如果从常规的或者制度化的视角来看,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官员对于御史的监察弹劾还是很重视的,甚至非常畏惧的。例如,唐敬宗时,夏州节度使李祐“违制进马一百五十匹”,侍御史温造上奏“正衙弹劾”,李祐被吓得“股战流汗”,以致私下对人说“今日胆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
在古代政制结构中,相对于其他职官而言,监察官员因其职责而显得与众不同,即“御史”必须保持一种与各方利益无涉的独立地位,从而保障其监察、弹劾、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现实中,御史在履行监察职责时总要面对品秩高于己、权势重于己的朝廷重臣或者封疆大吏,即便如此,御史监察依然卓有成效,并且在古代政制构造中,形成了一种足以维持和稳定官僚结构体系的制衡力量。一般而言,国家治理的优劣,通常取决于设计优良的制度以及确保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人。诚如荀子所言:“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仅就治理国家而言,如果说荀子在强调“君子”方面是合理的,那么,他在轻视“法制”方面或许是失之偏颇的。在一个愈益庞大而繁杂的国家政制中,仅仅依靠君子“修身”自律来实现治理,已被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要有合理的制度与“君子”相辅相成,方有可能维持一个有序的官僚系统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自东汉以降,即开始在制度建构上尝试设计成一种“君子”与“监察”圆融的制度模式,并且在实践中一直影响着后世御史监察职能的独立行使。事实上,与其说“御史独坐”是官员个人行止之结果,倒不如说是政制构造与实践中的习惯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历史上看,至少从东汉以来的“御史独坐”已成为一种基本法政惯例。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享有相当的独立性,一方面,御史不应有过多的兼职,以免影响监察职责本身的切实履行;另一方面,御史监察无须经由御史台长官的批准,即可径行启动监察程序,例如,唐建中元年,“令御史得专弹劾,不复关白于中丞、大夫”,终以皇帝诏令的形式,授权御史专司监察弹劾,从而在监察机构内部实现了“御史独立监察”的制度化。由此可见,在御史个人的“修身”与合理的监察“制度”之间,还需要在政制运作中形成一种御史监察的独立性观念,以及有国家强力为后盾的、使监察独立观念得以实现的制度性保障。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古代中国的监察实践中,御史监察一方面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效,也积累了相当成功的经验。作为监察官员的御史,不仅履行着“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的职责,发挥着专有的监察职能以及对皇权的制衡作用,并且还取得了澄清吏治、保障平衡政制运作等显著的监察实效。同时,御史监察的独立性也有助于促使古代监察制度得以有效的良性运转。故而,“御史监察”正是源于历史和本土的中华法治文明的结晶。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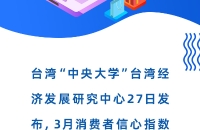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