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有兵书气自雄
腹有兵书气自雄
■刘 阳
1936年9月7日、9月26日、10月22日,毛泽东同志3次给我党驻东北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刘鼎写信,请其尽快送一些有关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兵书。收到所要的兵书后,毛泽东快读、细读,很有收获。
抗战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常读兵书,还组织人员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集结成《中国军事思想丛书》,供各级指挥员学习。同时,他还组建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研讨班,学习借鉴西方军事理论。
“胜利的总结里,除了宏大的原因,一些细节同样不能忽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对于当年的我军抗战,国民党一名高级将领曾说出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共产党军队除有坚强之领导、极端之英勇,难能可贵并急需我们学习之处是,他们始终重视学习科技和兵法。
兵书,研胜战之著作,是兵家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蕴含胜战之谋、砺卒之智、治兵之策;兵书,兵必读之著述,是哺育军人和将帅成长的乳汁。军人,尤其是肩负“统率千军之大任”的指挥员,腹有兵书气自雄,“观兵书战策多也”。
从古至今,战场上的决胜之道,往往始于案头上的方寸之间。一个真正谋战向战的军人,无不对兵书“读习而后得”,无不是“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正如吴子所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晨练宝剑,夜读兵书”,是卓越战将的一种常态。像王翦,“每日战毕,必秉灶夜读兵书”;像狄青,“晨闻鸡起舞,夜烛读兵书”;像朱可夫,“对各大国军事著作均有一定研读”。
“熟读兵书,深谙兵法”,是优秀名将的一种追求。像岳飞,“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以习之”;像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征战随身携带《亚历山大远征记》。
“熟读兵书百卷,韬略生焉。”革命战争年代,纵是戎马倥偬,军事政务繁忙至极,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跟毛泽东同志一样,不放弃学习兵书。
刘伯承同志博学勤学兵书,对许多名篇都能熟背。朱德同志称赞他“有古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邓小平同志赞颂他“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陈毅同志写诗表扬他“苦学入梦寐”。
1942年,彭雪枫同志在写给妻子林颖的信中说:“《战争论》是一部名著,我已经读了二分之一了,原定于半月包本,不,五天即读一半,倘无他事耽搁,十天内当可完工。”
粟裕同志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博览兵书,潜心钻研,并把自己的所学应用于战争实践,攻无不克,被誉为“常胜将军”。
周士第同志对兵书手不释卷,翻阅其读过的《读史兵略》,蝇头行楷的批注里,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千余字,所得所悟给人启示。
王近山同志的背囊和案头,军事书一大摞:《斯巴达克斯》《太平洋争夺战》《孙子兵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读兵书,既须温故,更须知新。“尽信书”,必然输。三国时期,马谡把兵书上的“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奉为圭臬,致使“置之死地”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唐朝时,房琯曾在山里苦读10年兵书,却在“安史之乱”中不知随机应变,居然用中原古战车法去对决沙漠骑兵,结果大败。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任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应是对兵书的态度。战胜不复,形于无穷。正如《武经七书直解》对读兵书的要求:读兵书,要下手从实做工夫,要将名将行过事迹体贴分晓,先要识得虚实,要知多方以误之之法……
“武而不文,不可称雄”“人读等身书,如将兵十万”。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吟诵唐人殷文圭的《赠战将》:“阵前战马黄金勒,架上兵书白玉签。不为已为儒弟子,好依门下学韬钤。”饱读兵书战策,深研军机戎事,使那一卷卷伴青灯黄卷书写的兵书,在结合实践、学以致用中不断吞吐出新时代的芳香。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责任编辑:唐诗絮
相关文章
军史钩沉
军史钩沉2022-04-14 16:48:38军史教育路上“追光者”
军史钩沉2023-01-10 10:57:25军史瞬间
军史钩沉2024-04-01 11:34:10每名党员都是党史军史书写者
军史钩沉2021-02-01 11:04:50从党史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军史钩沉2024-12-12 09:35:07用军史学习教育滋养战斗精神
军史钩沉2024-07-05 09:06:14图文军史馆
军史钩沉2024-04-01 11:34:48军史馆里忆往昔励斗志
军史钩沉2022-09-28 09:51:41军史文物|《战伤疗法》
军史钩沉2023-02-17 15:55:17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穿越时空的奋进乐章
军史钩沉2023-08-24 15:32:02
军情热议
逐梦星河!神舟二十在“中国航天日”发射成功!
4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中国载人航天在“东方红一号”发射55载之际开启第20次神舟问天之旅。神舟二十号...未来战场,无人机能完全替代有人机作战吗?
当前,军事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智能化、无人化作战趋势明显,世界各国纷纷加快无人装备研发速度,意图抢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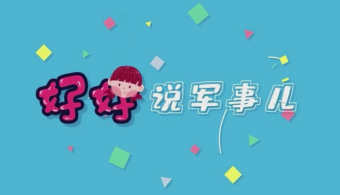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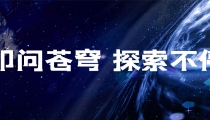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