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归国后奉敕著述的一部西域史书。该书为贞观三年(629年)至十九年玄奘的西行见闻,记载大量西域山川交通、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是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宗教信仰,中外交通、风土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季羡林称它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林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但它在古代中国的流传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诸多起伏,方成为世人皆知的一部中国经典。
唐之前的王朝对遥远的西域了解不多,仅有的知识来自《史记》《汉书》等典籍,缺乏实地资料。贞观十八年(644年),一心开拓西域边疆,但苦于毫无资料的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的消息,即派遣左仆射房玄龄、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等将其迎入长安。随即唐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召见玄奘,迫切询问西域地理交通、风土风俗等事,并郑重嘱咐玄奘编撰一部关于西域的史书,可见他对这部西域见闻记寄予厚望。
贞观二十年(646年),《大唐西域记》编撰完成。玄奘在《进〈西域记〉表》中极力褒奖了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大唐疆域广阔,超越前代,文治武功的盛世必须载入史册。该书看似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实则是大唐福泽四海的最好见证。
但此时唐太宗刚征伐辽东失败,心情郁闷,再加上李勣平定西域,诸部“乞置汉官”“遣使朝贡”,西域边疆态势有所好转,《大唐西域记》的现实意义随之下降。故唐太宗在《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中除盛赞玄奘的高风亮节、求法艰难外,对《大唐西域记》只简单写道“当自批览”。
唐初官方对《大唐西域记》的流传仅见于赠送西州刺史麹智湛、供王玄策出使西域使用、编修《西域图经》三处,民间社会更无迹可寻,可见其流传不广。
唐中晚期,随着文人士族、百姓僧众对西域认知渴望的加深,《大唐西域记》在唐中晚期社会的流传有了新的变化,影响逐渐增强。这一时期,《大唐西域记》逐渐进入文人士族的视野,笔记小说、经史典籍或直接引用《大唐西域记》,或以此创作文学、考证史地。元和年间刘肃以唐初以来名士言行纂成《大唐新语》,其中《记异》篇记载玄奘身世行迹、求法翻译史事,并简要介绍《大唐西域记》的情况。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记载天宝年间中岳道士顾玄绩事迹,亦以《大唐西域记》所记婆罗痆斯国救命池之说佐证其真实性。可见,《大唐西域记》已进入中唐文人士族视野中,成为文坛常见的史料,为世人熟知。
《大唐西域记》在中晚唐广泛流传。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唐传奇由志怪小说演化而来,中唐时进入创作高峰阶段,它以“变异”“传奇”为主要议题,内容奇幻、情节离奇,具有超脱现实的丰富想象力。隋唐时期胡风兴盛,影响颇深,中唐时达官贵戚、文士民众对西域文化的了解探求达至热潮,记载有西域风物、域外传说、神话故事的《大唐西域记》作为西域实录与异域文学的完美结合体,被传奇作者青睐有加,其中的西域故事传说被改造入唐传奇之中,更能引起文人士族、民众百姓对《大唐西域记》的好奇与追捧。
唐以降,《大唐西域记》更加广为流传,它的真实记载、古怪离奇的民间故事、绚丽多彩的域外风情,以及简扼流畅的文笔,都令人读来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爱不释手,在佛教僧众、文人士族、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焦竑《国史经籍志》、丁仁《八千卷楼书目》等私人藏书目录多著录此书。《大唐西域记》的丰富内容甚至还为明代吴承恩创作中国经典神话小说《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历史基础。这些都表现出宋元明清时人们对《大唐西域记》具有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促进纸本文献传播进入了“大发展”时代。宋元明清时《大藏经》仿效《开元释教录》,多收录《大唐西域记》。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发展,宋《崇宁藏》《资福藏》《碛砂藏》、金《赵城金藏》、元《普宁藏》、明《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清《龙藏》以几何级速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传播。这些《大藏经》均收录有《大唐西域记》,便利了此书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促使更多人看到《大唐西域记》。
其次,宋元明清佛教世俗化的加深使文人民众接受佛教文史作品成为一种常态,使《大唐西域记》在宋元明清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宋元明清佛教最大的特点就是佛教世俗化进一步加深,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者众多,佛教广为流传、深入民心,上至帝王皇室、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多有信佛之人。正如宋代陆九渊说:“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说皆足以动人,士大夫鲜不溺焉。”亦如陈垣评价明代士绅喜爱佛教所言:“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至于百姓信仰佛教之风更是盛行,人们纷纷以烧香拜佛、布施斋僧、念经抄文、吃素放生等方式来表现信佛之心。尤其是明代佛教复兴后,文士群体阅读佛教书籍成为潮流,《大唐西域记》随之受到重视。明人周嘉胄《香乘》以《大唐西域记》介绍龙脑香等物产。《戒庵老人漫笔》比对婆罗痆斯国隐士与杜子春故事。这些都与宋元明清佛教世俗化加深有很大关系,进而影响到《大唐西域记》的流传。
最后,随着明清西域边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记载西域风土人情的《大唐西域记》亦成为官方关注西北问题的参考文献。如清《四库全书总目》称《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尤不足稽”,但“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清代学者也多借此书考证、勘误西北名物、史地,如金永森《西被考略》、李光廷《汉西域图考》、魏源《海国图志》、俞浩《西域考古录》等书均大量征引《大唐西域记》史料。晚清时期,张之洞因“要典雅记、考求论定”,为士子作《书目答问》,也将《大唐西域记》列入子部释道家必读之书。这些都表明《大唐西域记》在宋元明清仍然广为流传,受到官方和文人士族的关注,为宋元明清的文学创作、西北史地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大唐西域记》后世传入日本,汉学家儒莲亦将其译为法文,流传于全世界,《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文明沟通的见证。可以说,《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时代与疆域,也为中外文明交融共生提供了优质案例与历史启迪。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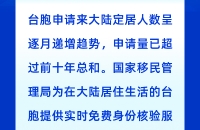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