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英雄礼赞
■李晨昕 奉云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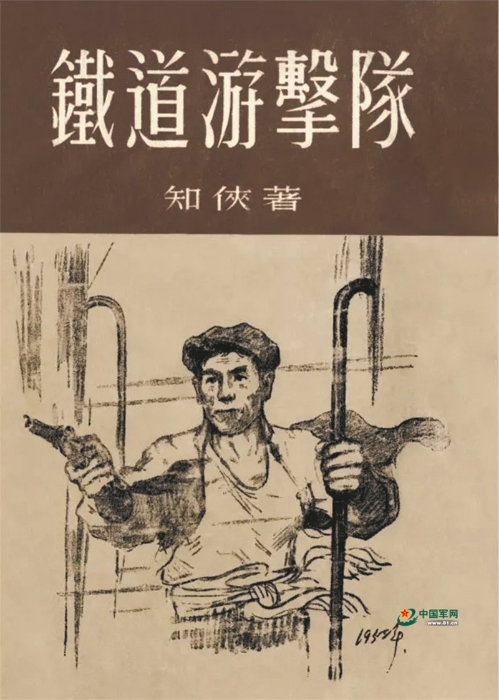
1954年出版的《铁道游击队》。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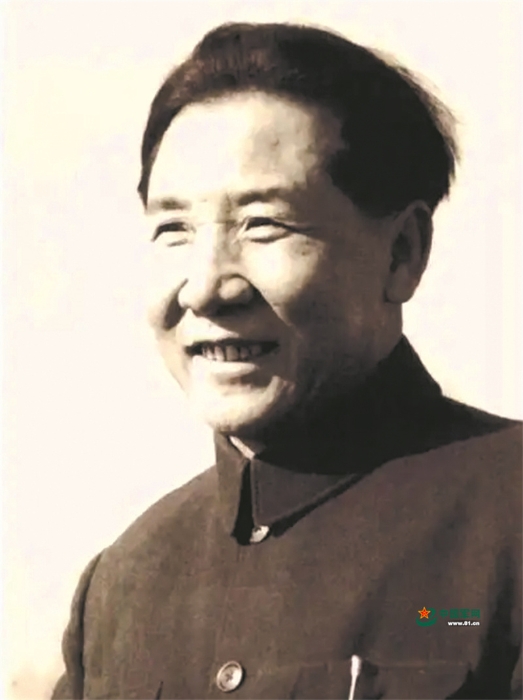
刘知侠。资料图片
传播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地区(今山东枣庄一带)活跃着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鲁南军区铁道大队。这支被日军称为“从天而降的飞虎队”的队伍,以津浦线、临枣支线等长达百余里的铁道线为阵地,与敌展开顽强而机智的斗争。他们隐匿于万顷微山湖中,在敌人核心区域坚持战斗7年时间,经历战斗百余次,促进了抗战形势的发展。
作家刘知侠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1954年1月,《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还曾在社会各界形成了“读‘铁道’、忆抗战”的热潮。
1956年,《铁道游击队》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为同名电影,由刘知侠亲自担任编剧。片中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由歌唱家陈景熹演唱。该曲具有浓郁的山东民歌特点,节奏从抒情慢拍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是抗战题材电影插曲的代表作之一。
该小说在1985年和2005年,分别被改编摄制为12集和35集电视连续剧;1995年和2021年,分别被改编并拍摄成电影《飞虎队》和《铁道英雄》,这使得《铁道游击队》的热潮持续升温,直到今天仍受到大众的推崇和喜爱。2019年,《铁道游击队》入选由学习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10家出版单位策划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
作品片段
十个指头紧紧钳住窄窄的铁棱,手指所用的力气,要是抓在土墙上,足可抓进去,穿上十个窟窿。但是,这是铁板,铁板坚硬地顶住他的指头,他的指甲象(像)被顶进肉里去,痛得他心跳,但是他不能松手。急风又象(像)铁扫帚一样扫着他,象(像)是要用力把他扯下去似的,下边是车轮和铁轨摩擦的刺耳的声音。只要他一松手,风会立刻把他卷进车底,压成肉泥——甩到车外也会甩成肉饼。他拼命扒着,头上的汗在哗哗地流,他咬紧了牙根支持着。
——《铁道游击队》第二章
可是当他们看到屋当门,空着的那桌酒菜和桌正面墙上牺牲同志的牌位时,眼睛里又都充满了悼念之情。他们想起了林忠、鲁汉、老张、冯老头,还有王虎、张兰……这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和同志。这些同志的面貌和英勇的姿态,马上闪进他们的脑际,使他们又想到多年来,在临枣支线,微山湖边的火热的对敌斗争。在残酷的战斗里,他们透过火光和枪声,看到湖边和铁路两侧的人民,遭受着鬼子的烧杀抢掠,陷入难言的苦难。为了战斗的胜利,有多少好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现在胜利来到了,可是这胜利是多少抗日军民的血泪换来的啊!
——《铁道游击队》第二十八章
作家心语
我认为我是有条件写好这一作品的。第一,我在抗大毕业后, 又专学过军事。1938年到1939年我随抗大一分校从陕北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两次深入敌后,熟悉敌后的游击战争生活。第二,我熟悉铁路上的生活。我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道清支线的铁路边。这条铁路从我故乡的村边经过,我的父亲又在村边的铁路道班房里作工,我一天到晚能看到客车、货加车在运行, 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运行的轧轧声。
……
我走遍了湖边和铁路两侧,寻访了他们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我曾在姜集附近的运河边的一块小高地上,站立了好久,听着他们叙述一次难忘的战斗。当时他们在这里隔着狭窄的运河, 和一小队日本鬼子在进行血战。战斗是炽烈的,隔岸的一小队鬼子、小队长被他们打死了,这队鬼子几乎全部被他们歼灭。可是另两路鬼子迅猛地向这里扑来。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最最心爱的大队长洪振海在这高地上牺牲了。我俯视着洒了老洪鲜血的这块土地,枯黄的草丛下边已冒出嫩芽。我站在那里,久久不能平静。
……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日寇投降后,游击队员们第一次的新年会餐。在庆祝胜利的丰饶的酒席上,正象(像)我小说里第二十八章所写的那样,他们是以古老的形式,来悼念自己牺牲的战友。他们把一桌最丰满的酒菜,摆在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前边。他们平时喝酒喜欢猜拳行令,可是在这一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却都沉默着喝闷酒。他们隔着酒桌,望着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眼里就注满了泪水。哪怕在最欢乐的时候,一提到已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就会痛哭流涕。当时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
……
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
所有这一切,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情和勇气。可是写出后,自己再看一遍,又使我很不安,总觉得我所写的,远不如他们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彩。
当代视角
历史真实与传奇叙事的交融
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以其独特的叙事张力和深刻的精神内涵,成为新中国军事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这部承载着民族记忆的作品,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建构,再现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抗战传奇故事,在几代人心里留下了美好记忆。
《铁道游击队》的文学价值,集中体现于对中国传统传奇叙事的创造性转化。作者刘知侠在继承章回体小说“设悬念、重巧合、强动作”的美学传统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解构为“飞车夺机枪”“血染洋行”等一系列充满戏剧化的场景。这种传奇化叙事并非是脱离现实的虚构,而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之上。作者在本书“后记”中写道,《铁道游击队》“是以他们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骼,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
作者刘知侠曾长时间深入到铁道游击队战斗生活一线,和官兵同食宿、共战斗,走过了很多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他甚至不顾生命危险,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亲眼目睹战士们是如何豁出性命扒上火车,同敌人真刀真枪展开战斗。这段经历,使他对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生活和思想情感有了真切而深刻的体会。这种“在场性”的创作姿态,使得文本在具有文学想象力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纪实品格。因此,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比如,铁道游击队先后有4人担任过政委,作者根据他们的个性特点,以杜季伟为主塑造了小说中李正这一形象。再比如,“芳林嫂”的原型也有3位,分别是时大嫂、尹大嫂和刘桂清。作者融合她们的个性特点和斗争事迹,塑造了“芳林嫂”这一朴实的革命妇女形象。
尽管作者坦言对原始素材进行了“艺术选择与重组”,但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伦理。作者并没有为了歌颂英雄伟绩而一味拔高,也没有回避鲁南当地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游击队员自身在精神心理、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不足,而是从现实视角出发,遵循生活本身的逻辑。
鲁南军区铁道大队成立之初,队员寥寥无几,驻扎在煤炭资源丰富、日军重点防范的枣庄地区,其斗争方式只能是以小博大、出奇制胜。他们巧妙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民众的支持在敌占区灵活穿梭,并通过扒火车、炸桥梁等独特方式,有效打击了日军的物资运输线。此外,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取了“一波三折”“转危为安”“无巧不成书”等传统叙事策略,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奇巧,将鲁南军区铁道大队“以弱制强”的战术智慧转化为充满戏剧张力的文学场景,建构起“革命传奇”这一独特的叙事模式。
《铁道游击队》之所以家喻户晓,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诉求。该小说不仅契合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塑民族认同的历史需求,更在深层结构上呼应着传统侠义精神向革命英雄主义的现代转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他们既是“泥土中走出的英雄”,带着底层民众的生活印记,又在党的培养和战争的锤炼下,逐渐成长为具有集体意识的革命战士。小说通过具体的战斗故事,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这一宏大历史命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形象,使传奇叙事成为诠释革命历史的生动注脚。
从当代的视角看,《铁道游击队》的价值超越了“红色经典”的范畴,成为探讨文学如何处理历史记忆、塑造英雄形象、回应时代精神的重要样本。这部作品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深刻启示:唯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让文艺作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广泛的影响力,才能具备所处时代的标志性和辨识度;只有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官兵,才能在强军征程中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实现军旅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攀登。
作者:李晨昕 奉云鹤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责任编辑:唐诗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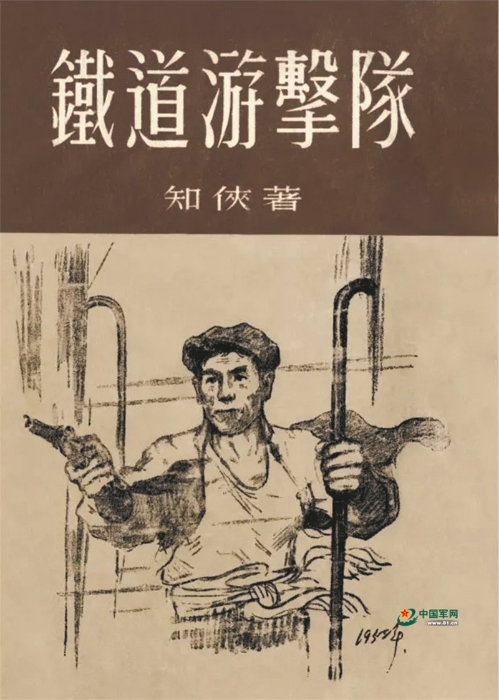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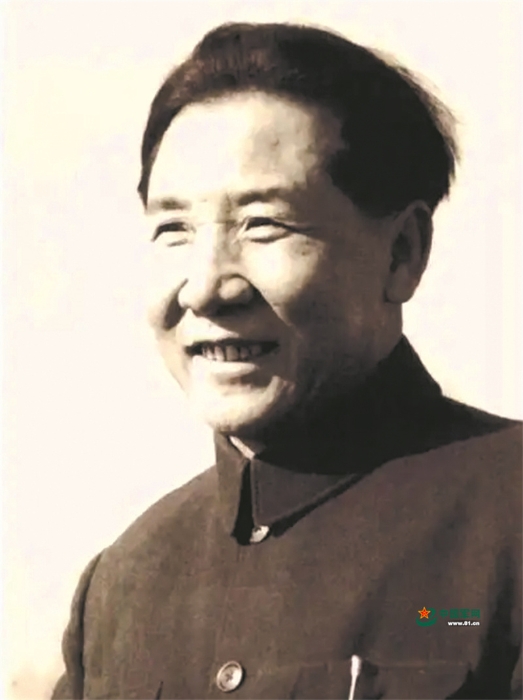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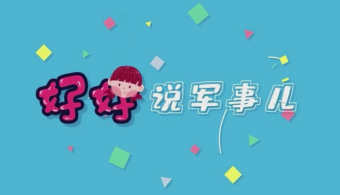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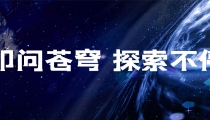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