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思想资源
“大一统”观作为中国历史理论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今人或将“大一统”观简单理解为中央政权拓展并控制广袤疆域的空间概念,仅观察到了“大一统”观中的“大统一”这一维度。其实,“大一统”观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是中国古代“正统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一统”观的重要作用在于诠释王朝统治正当性,亦即中国古代所谓“正统”。“大一统”观出自《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这一《春秋》经文的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代公羊学家对此有繁复的解释,其基本意涵可被概括为:受命于天的王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实施制度变革,构造出自上天至人世的上下贯通、政教合一的体系。故依“大一统”理论而言,帝王及其制度都有“天命”作为根据,具备十足的道德正当性。
清代是“大一统”观发展和实践的关键阶段,这与清朝满洲统治者克服“夷狄”的身份焦虑、获得“正统”资格密切相关。宋明两代长期与所谓“夷狄”对峙,实际领土范围不及汉唐,难以实现统合“华夷”的大一统,故其“正统性”论述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只强调“正统论”之正,而暂时搁置疆域拓展这个维度。清朝统治者既着力批判“夷夏之辨”,又有意鼓励士林超越宋明理学而回归汉代经学,从而重新发掘、解读古代“正统论”中的“大一统”观的思想意涵。
清代“大一统”观的重要特征在于,在统治超越宋明的广袤疆域基础上,又为“正统性”融入多民族的因素,使得“正统性”呈现多民族交融的多样化特征。一方面,清朝在皇家礼仪中,祭祀源于多重民族的神明,寻求多种文化传统的交融;另一方面,清朝为统治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和西藏地区,选择尊崇藏传佛教,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藏传佛教为辅的“正统性”格局。这种多样化的“正统性”被清朝君臣置于对“大一统”观的再诠释中,并未游离儒家思想的传承脉络,已呈现后来我们所说的“多元一体”特征。
上述清代“多元一体”的“大一统”观,又改造了宋明以来的“中国观”,形成了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大中国”概念。宋明君臣的“中国”多指汉地,“夷狄”之地作为“化外”常不被包含其中。雍正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这里所谓“中国”,仍取宋明时代的“汉地中国”之意。但是,又如雍正帝所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即经由清朝“大一统”观对“中国”和“塞外”的统合,一个融合多民族的“大中国”概念逐渐形成。同样著名的案例是,在清朝自康熙以降的对外谈判中,“中国”常被作为“大清国”的同义词,“大清国”之领土人民亦即“中国”之领土人民。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其诏书称“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代“大一统”观塑造的“大中国”更在法理上被继承下来。
正因如此,晚清以降,虽然“大一统”观遭到质疑和挑战,被批评为与清朝实行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紧密相关;但是“大一统”观原先发挥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而是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重要传统资源。
1902年,梁启超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最终成为指涉中国内部所有民族的概念。如前所述,这本就是清代“大一统”观塑造“大中国”的结果。然而,关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内部“一”与“多”的关系,仍存在不同观点。与此相关,面对近代以来的外来入侵与民族危机,如何有效维系清代“大一统”观塑造的遗产、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亦是时人迫切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抗战期间,围绕“中华民族”性质的争论便反映了“大一统”观与现代国家观的冲突与调适过程。在这次争论中,顾颉刚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否认中国境内存在多个民族,强调抗日危机局势下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则主张“团结各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费孝通亦强调民族平等的价值与不同族群文化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国民党则提出“中华民族宗族论”,认为国内各民族不是各自独立的民族,而是属于有着共同血缘的不同宗族。这类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如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推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民族平等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吴文藻与费孝通的上述观点,便与这一系列政策取向契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清朝对藩部的治理经验。费孝通在1980年代更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这一理论既与清朝阐发的民族观有相似之处,又是对清朝“大一统”多民族共存观念的改造升级。例如,费孝通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分为“自在”与“自觉”两个阶段。首先,费孝通否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之辨”,接近清朝“中外一家”的民族观,且肯定中国历史上形成“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从而接纳了“大一统”观尤其是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清朝“大一统”观留下的遗产。其次,费孝通强调,“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并认为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从而为“大一统”观赋予了现代意义。
总之,清代“大一统”观为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留下了丰厚遗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亦在相当程度上汲取了“大一统”观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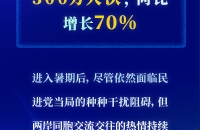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