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中的关陇雄风 ——北周如何奠基隋唐盛世
《周书》又名《后周书》,是唐代令狐德棻主持编纂,岑文本、崔仁师等参与修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的是从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承上启下的历史枢纽
北周虽国祚短暂,却在政治制度、军事体系、文化融合等方面深刻影响着隋唐格局,是连接南北朝与隋唐的核心枢纽。
北周统一进程奠定了隋唐大一统基础。西魏初期仅控制关陇地区,后期通过吞并后梁占据益州,疆域拓展至今四川、山西、湖北等地。577年,周武帝灭掉北齐,不仅统一了北方,更整合出一套强大的军事行政体系。隋朝继承北周疆域与实力后完成全国统一。
西魏北周制度改革构建隋唐政治军事体系框架。《周书·文帝纪下》记载:西魏初期受东魏高欢军事威胁,高氏凭借强大军力频繁入侵边境,意图吞并。面对关中多民族杂居的复杂局面,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揭示,这项政策通过融合胡汉各族,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治集团。八柱国统领二十四军的府兵制架构,不仅是隋唐军制的渊源,更催生出影响深远的关陇集团。正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述,周、隋、唐三代统治者皆出自武川军镇,这种军政集团的延续性成为理解隋唐政治结构的关键。
西魏北周继承北魏历史遗产推动南北文化融合。西晋灭亡后,江左延续汉魏衣冠礼乐,北方则由鲜卑拓跋氏完成统一。北魏政权混合汉制与北族习俗,“为中原文化注入塞外精悍血液”,西魏北周将之整合为系统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认同的深度整合,为隋唐实现“华戎同轨”的文明气象奠定基础。
深入理解西魏北周的历史枢纽作用,《周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周书》作为核心史料,勾勒出西魏北周典章制度的发展脉络。卷二《文帝纪下》详录554年“改置州郡及县”的行政改革,成为研究地理沿革的关键文献;卷一六记载西魏二十四军的府兵结构,为理解早期府兵制提供基础;卷二四《卢辩传》梳理西魏北周官制,反映其虽仿《周礼》实则兼用秦汉旧制的特点;卷二三《苏绰传》完整收录“六条诏书”,揭示西魏北周政治纲领。
不仅局限于政权内部,也广泛记录周边动态,是《周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天下分裂,《周书》将东魏、北齐、梁陈兴衰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使读者对时局一目了然。卷四八为后梁三代君主及重臣立传,卷四九、五○《异域传》首次系统记载突厥、稽胡历史,保存了珍贵的民族史料。这种书写方式打破东西魏对峙、兼记南北政权,突出了北周“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
《周书》摒弃程式化文书,注重原始资料。卷一一《宇文护传》收录宇文护母子书信,成为研究中古社会史的重要素材。卷三一《韦孝宽传》记载“平齐三策”,主要研究论述北周的地缘战略。卷四一《庾信传》全文收录《哀江南赋》,这为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了经典文本。
作为记录西魏北周最原始的史籍,《周书》通过典章制度、政权互动、文献辑录等多维度的呈现,不仅让读者对西魏北周的历史全貌一目了然,也通过独特的编纂视角,对制度沿革、地缘战略与文化整合的深层脉络进行了有机融合。
北周遗产的隋唐转化
隋唐政权通过继承北周政治遗产确立自身正统性,这一过程深刻体现在《周书》的编纂中。唐初编撰《周书》的重要目的,是宣扬李唐先祖功业,构建“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的法统链条。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史书的编撰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确立西魏北周作为北魏继承者的正统地位;二是论证关陇政权向隋唐大一统王朝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北周正统性来源,首要问题涉及北魏分裂后的继承权之争。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高欢与宇文泰各自拥立北魏宗室,均以拓跋政权继承者自居。北齐天保二年编撰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隋文帝为适应政治需求,命魏澹重修《魏史》,确立“西魏为真,东魏为伪”的基调。《史通》记载此次修史“文恭列纪,孝靖称传”,从国家层面承认西魏合法性。唐初修史时,《周书》延续这一脉络,《周书·文帝纪》虽主要记述宇文泰功业,但始终使用西魏年号,通过串联北魏、西魏、北周谱系,构建完整的法统体系。相比较而言,《北齐书》仅在北齐建国历史中追溯北魏末年及东魏史事,缺乏正统建构的主动性。
探讨隋唐承接北周的历史脉络时,令狐德棻刻意采用了多种叙述方式,从政治合法性、制度渊源、历史记忆等多重角度展开阐释。令狐德棻在奏疏中明确强调李唐“复承周氏历数”,但北周并非统一政权,需通过历史书写强化其宗主地位。故而《周书》不仅记录西魏北周史事,还系统记载东魏北齐、梁陈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动态。如卷四八为后梁三代君主立传,卷四九、五○《异域传》详述对外交往,这种“天下共主”的书写模式,与《北齐书》局限于区域政权的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读者在字里行间自然形成北周疆域“包举宇内”的观念认知,从而成功塑造北周作为正统宗主国的形象,为隋唐继承其政治遗产铺平了道路。
此外,《周书》的编纂也深受唐初门阀政治影响。唐太宗命高士廉编《氏族志》时强调,只按照目前的官职爵位高低来确定等级。这一原则直接服务于“崇重今朝冠冕”的政治目标。令狐德棻同时参与《周书》与《氏族志》编修,在《周书》中特设“八柱国家”传记,直言“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这种书写既照顾了现实的政治需求,又通过追溯关陇集团的源流,充分构建了李唐与西魏北周的历史承袭关系。
通过以上编纂方式,《周书》成功地将北周这个割据政权转化为承魏启隋的关键枢纽。这种历史书写方式不仅确立了西魏北周的正统性,更通过谱系建构与门阀追溯等,为李唐政权提供了更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东西对峙的实力逆转
高欢和宇文泰均出身北魏边镇,在王朝末年的动荡中崛起为权臣,分别成为北齐、北周政权的奠基者。东、西魏分裂初期,东魏凭借富庶占据优势,但最终西魏逐渐强盛,北周更灭北齐统一北方,为隋朝统一奠定基础。这一逆转,与双方治国策略及北方民族局势密切相关。
二者的差异,首先体现在经济与社会治理上。东魏北齐占据关东富饶之地,却纵容豪强兼并土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记载,天保年间官府曾强征民田充公,但后期又将土地赏赐给权贵外戚,导致肥沃土地尽归豪强,普通百姓无田可耕。《通典·食货典》指出,这种状况造成富人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隋书·食货志》更称隋初山东地区沿袭北齐陋习,逃避劳役与游手好闲者占人口六七成。同时,北齐大兴佛教,寺院不仅占据大量良田,还收容依附人口。此类行为严重削弱了国家财力。
反观西魏北周,宇文泰面对关中经济凋敝的现实,推行均田制分配土地,创建府兵制强化军队,试图凝聚民心。谋臣苏绰提出平均赋税劳役的政策,意在遏制豪强扩张。据《广弘明集》记载,周武帝灭佛后,原属寺院的土地人口重归国家,使得百姓劳役减轻,税收连年增长,军队日渐强盛。这些举措彻底扭转了两方的实力差距。
政治整合与内部分裂更是推动二者走向不同的结局。北齐始终未能化解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其权力结构呈现“胡——汉”“邺城——晋阳”双重对立的局面。《北齐书·神武纪下》记载,权臣侯景曾公开表示:若高王在世,我尚能效忠;若高王不在了,我绝不与鲜卑小儿共事。这个话暴露了统治阶层的分裂隐患。到了北齐后期,文官祖珽利用谣言陷害名将斛律光,史官痛惜此举令将领离心,反助敌国复仇。相比之下,西魏北周通过关陇集团融合各方势力,宇文泰及其继任者持续推行改革,保持了统治集团凝聚力。
军事态势转变直接反映了历史结构发生的变化。《北史·斛律光传》记载了一个标志性细节:北齐文宣帝时期,周军因惧怕齐军冬季踏冰渡河进攻,每年都要凿开黄河冰面;但到北齐武成帝时,双方攻守易势,变成齐军凿冰防御周军进攻。这种转变明显体现了双方实力的逆转。
北方游牧势力的消长深刻影响东西战局。北魏分裂后,柔然与东魏结盟压制西魏。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西魏通过联姻与之结盟,而北齐选择支持柔然。《周书·突厥传》记载:552年,突厥灭柔然后,北周联合突厥对抗北齐,形成夹击之势。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理论,恰可解释突厥崛起对北齐灭亡的重要作用。
综上,西魏北周通过土地改革、军政整合将潜力转化为实力;北齐则因土地兼并、内斗不止持续衰弱。加之突厥崛起改变地缘格局,最终推动“东强西弱”形势彻底逆转。这一历史进程也是我们认识北周平齐乃至隋唐统一全国这段历史不可忽略的一个侧面。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邱梦颖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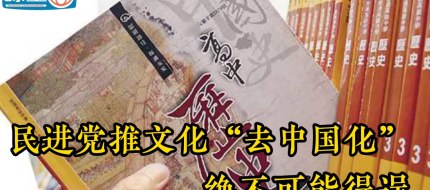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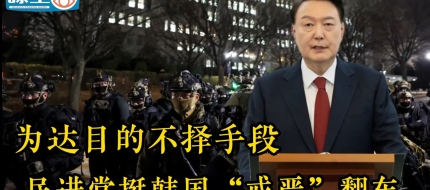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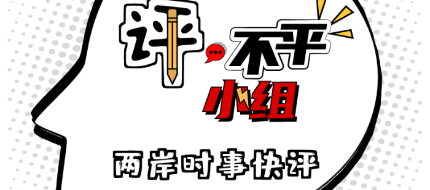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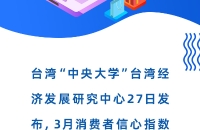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