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东阳马生序》:一部情理交融的劝学篇
《送东阳马生序》是明代宋濂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篇赠序体散文,它不仅承载了深厚的文学底蕴,还通过生动的叙事、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语言艺术,展现了宋濂的儒家教育理念。
文本结构与叙事策略
《送东阳马生序》具有严谨的结构与巧妙的叙事策略。整篇文章围绕“劝学”这一主题展开,采用“自述—对比—劝诫”的三段式结构,层层递进地揭示了自己对于学习的理解与体悟,从而构建了一部情理交融的劝学篇章。
文章以自述寒窗苦读为开篇,设置了情感的基调。宋濂通过“余幼时即嗜学”来引出自己对学问的渴望,并回忆了自己少年时期的艰难求学经历。诸如“假借藏书”“趋百里问师”“负箧曳屣”等细节的描写,生动刻画了一个寒士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依然不改求学的志向。这些细节不仅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与代入感,也让读者感同身受,感受到学习道路的艰难与执着。
以“今诸生学于太学”为转折,文章通过对比手法,讲述了当下太学生的优越求学环境。列举了“廪食”“典籍”“师资”等方面的优渥条件,突显出自己曾经的困顿与当下求学环境的富足。这种对比并非简单批判,而是通过反差,指出即便在优越条件下,如果没有足够的专注与努力,也难以取得学业上的成就。进而指出文章的核心观点,学业不精、品德不成,不是取决于天赋,而是取决于个人的专心致志和努力。
宋濂在此以“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作为收尾,通过赠言劝学的方式,完成了从个体经验到普遍意义教化的跨越。将自己在寒窗中的奋斗历程升华为共通性价值的教诲,强调心无旁骛的劝学精神。这一部分的写作策略,通过个人经验的分享,使得整篇文章不只是对马生的劝勉,更是一种对所有学子的普遍呼吁。他强调通过专心致志的学习才能成就学业与人生这一训诫,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更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智慧。从个体叙事延展到群体教化,劝学的主题也具有了广泛的道德性与共通性。
思想内涵的多重维度
宋濂在追忆早年求学经历时,“立侍左右”“俯身倾耳以请”等细节描写,生动再现了传统儒者的求学之道。这些看似简单的肢体语言,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为学之理,侍立时的专注姿态,体现着对知识的敬畏;俯身时的谦卑举止,彰显着求知的诚意。这种将身心完全投入学问的态度,正是宋濂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重要根基。其背后所遵循的,正是《礼记·学记》中“师严然后道尊”的为学准则,唯有确立师道的庄严,学问的真谛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承。
文章中“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的自述,诠释了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正是对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切身实践,在物质匮乏的处境中,他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热忱,将精神追求置于物质享受之上。宋濂以自身经历表明,真正的儒者能够在清贫中坚守求知的初心,通过克制物欲来成就德行。
宋濂从“家贫,无从致书以观”的困境起步,到最终位列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这一跨越展现了科举时代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案例。在文章中,他对比自己当年的艰苦求学与当下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揭示了个体通过知识获取功名的价值,也反映了明初科举复兴背景下寒门士子实现阶层跃升的普遍路径。
宋濂一方面真切记述“每假借于藏书之家”“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的求知困境,凸显了书籍资源这一外部条件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更着重指出“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这一观点,凸显了学习者主观能动性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既重视客观条件又不囿于客观限制的认知方式,超越了传统劝学文本中片面强调“囊萤映雪”的单一维度。这一见解与现代教育心理学中关于“刻意练习”和“成长型思维”的理论研究相契合,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超前性。
艺术特色与文体创新
与唐代文学家韩愈《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起兴的借古抒怀不同,宋濂以“余幼时即嗜学”的平实叙述,通过“手自笔录,计日以还”等细节描写,将个人求学经历转化为生动的劝学教材。韩愈以“董生勉乎哉”的抒情笔调抒发离情别绪,而宋濂则以“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直白地进行表述。这种以真实经历为基础、以劝勉后学为目标的写作方式,使赠序从多抒离情、重文学性的传统范式转变为具有实际教育意义的文本,反映了明代士人注重经世致用的观念。
宋濂以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与元末“玉山雅集”“铁崖风流”等纤秾缛丽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文中“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的平实叙述,摒弃了雕琢修饰,以白描手法再现寒门学子的求学场景。这种简朴自然的表达,与归有光《寒花葬志》中“曳深绿布裳”等细节描写异曲同工,都体现了返璞归真的审美追求。这种语言风格的转变,既矫正了元末文学过度“缘情”的倾向,又开创了明代散文的新风貌,展现了明初“雅正”文风的独特价值。
文章巧妙运用多重对比手法,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劝学体系。本文通过“手自笔录”与“今诸生学于太学”的今昔对比,展现了求学环境的差异;以“缊袍敝衣”与“同舍生皆被绮绣”的物质对比,凸显了精神追求的可贵;更以“俯身倾耳以请”的谦卑态度与“门人弟子填其室”的求学盛况相对照,强调学习态度的重要性。这些对比层层递进,最终归结于“心不若余之专耳”的核心论点,使劝学主题自然显现。
历史语境与创作动机
作为致仕归乡的帝师,宋濂以“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的谦逊姿态向后学传授经验;作为文坛领袖,又通过“预君子之列”“承天子之宠光”等表述,完成了对自身儒者身份的终极确认。这种双重身份的融合,使宋濂既有“日侍坐备顾问”的庙堂高度,又饱含“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的师者情怀,展现了明代士大夫在仕与隐之间的精神追求。
文章中“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的记述,呼应了明初“治国以教化为先”的国策。文中“承天子之宠光”的表述,既是对朱元璋文教政策的认同,也暗含对朝廷教化方针的赞许。这种书写巧妙地将个人求学经历与明初文教建设相结合,通过“有司业、博士为之师”等细节,展现了当时教育体系的发展。
文章中“益慕圣贤之道”的表述,与其《文原》“尧、舜、文王、孔子之文”的主张一脉相承,体现了金华学派“明理躬行”的学术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在强调博览群书的同时,又以“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点明治学要旨,这种既重博览又强调专精的治学态度,深植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中“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的治学理念,并在实践中实现了方法论层面的拓展与创新。
学术史评价与当代价值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自清初以来逐渐成为散文典范,其经典地位在历代文论中得到持续确认。清人评点中“以常情写至性”的审美判断,恰切概括了文本白描叙事的艺术特质。现代学界普遍关注文中展现的知识伦理,认为其通过个体经验折射出的治学精神,至今仍具启示意义。面对当代教育困境,文中“以中有足乐者”的治学态度,为“内卷”时代的学子提供了返璞归真的精神参照。而宋濂的寒门奋斗叙事,既彰显个人奋斗的价值,也引发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深层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借书”与“程门立雪”的典故互为映照,共同塑造了儒家文化中求学问道的典范形象。这些文化符号通过教材、典故等形式持续传承,其精神内核在当代教育语境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邱梦颖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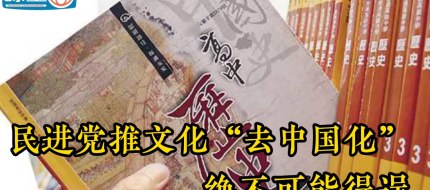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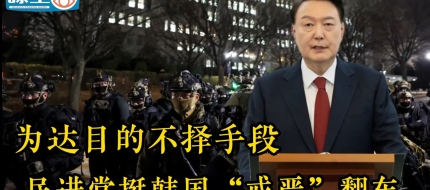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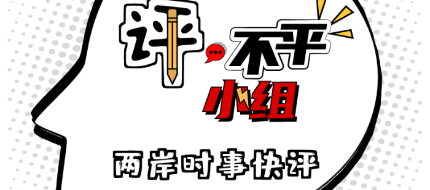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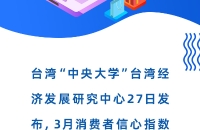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