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台遗址:秦汉海洋文明蓬勃发展的重要标识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遗址三面临海,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据文献记载,琅琊与齐地八神“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东巡等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自2019年主动性发掘工作启动以来,考古人员确认位于遗址中心、面积达45000平方米的山顶夯土为“秦修汉葺”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在基址东、西两侧发现附属房间、石铺道路及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并于山南发现年代明确的秦代窑址,以及与山顶建筑同时营建、边长约120米的正方形院落。此外,在遗址东南部还发现了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建筑群。遗址内各主要遗存地点共同构成一处长时期延续的滨海高等级建筑群落。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四次东巡皆至于海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石刻上有“事已大毕,乃临于海”语句,标志着秦朝已完成统一大业,从真正意义上将海洋纳入国家政治视野。琅琊台遗址的诸多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历史文献中关于秦皇汉武东巡的记载,更以实物证据展现了秦汉对东方海疆的治理策略,以及秦汉时期日益浓厚的海洋意识和蓬勃发展的海洋实践。
“海畔高台”:面向大海的国家工程。考古发现的山顶高台建筑,夯土基址体量宏大,施工标准极高,出土了夔纹大瓦当、龙纹踏步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此类遗物仅见于陕西秦始皇陵、辽宁姜女石秦行宫等与秦始皇密切相关的遗址,表明琅琊台建筑为秦代最高级别的国家工程。
目前考古发掘成果显示,琅琊台遗址内的重要建筑均以海洋为主要朝向。位于遗址核心和制高点的山顶高台建筑,其东侧相较于其他三面,面积最大、层级最多,此处房间、院落门道均朝向大海。考古人员在建筑东部发现长约15米、宽约2米的石铺路面,推测为面东殿堂前的场地,是观海远望的绝佳地点。山南院落则选址于背山面海的高亢阶地上,主要建筑面朝南,可尽览南方海域。山顶与山下建筑历经秦与西汉,虽经过多次整修,但基本朝向未变。
秦汉统治者对海洋尤为关注,并以博大的胸怀和视角看待海洋。此时的海洋已不再仅仅作为国家的边界,而是亟待探索的新领域。琅琊台建筑作为国家工程,生动体现了秦汉时期向海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
“临照于海”:巩固海疆的治理策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乃抚东土”,东巡的主旨在于宣示统治威权。其四次巡视沿海地区,路线南起浙江、北至辽宁,涉及中国多半海岸线,足见对于海疆高度重视。东巡途中,秦始皇在重要驻跸地点大兴土木,并留下石刻,以此彰显对新疆域的统治。建成后的琅琊台雄踞海畔山巅,成为秦始皇统治东方的重要象征。
秦始皇以修琅琊台为名,“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推测移民人数可达十万之众。从建筑基址的巨大体量以及专业化的砖瓦窑址来看,其对劳动力的数量和技术水平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势必需要大量外来人口的支撑。有组织的移民不仅为大型工程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沿海地区开发提供了人力基础,反映了秦朝对海疆治理的系统性考量。
秦并天下设三十六郡,琅琊郡为其一。郡县制的实施极大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调查显示,今琅琊镇及其周围存在一处较大规模的秦汉时期聚落,其与琅琊台之间有道路相通,极可能为秦琅琊郡城所在。在新的行政制度管理下,滨海地区人口结构和文化面貌出现巨大变化。在遗址发掘和周边调查中发现不同文化类型的遗物并存,尤其是来自秦汉统治中心,体现中央政治制度、生产工艺和文化风格的遗存大量出现,折射出海疆开发带来的多元文化融合效应。
“礼祠八主”:源于海滨的国家祭祀。相较于生活于西部内陆的周人、秦人,坐拥山东半岛的齐人直接接触大海,在享受“鱼盐之利”的同时,也形成了与海洋密切相关的思想意识。齐地“八神主”信仰体系中,“日”“月”“阴”“阳”及“四时”等多数神主的祭祀地都位于滨海地带,这应是齐人在向东扩张进程中吸收半岛土著原有自然神信仰并加以改造整合的结果。这些信仰蕴含了早期人类对包括海洋在内的自然界的认识,是沿海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映射。
《史记·封禅书》载齐地八神中“四时主,祠琅邪”。琅琊台遗址东南部的亭子兰地点,发现了由长廊和院落构成的战国时期建筑群。建筑群濒海而建,规模庞大且形制独特,出土器物具有齐文化特征,应是齐国经营琅琊时期重要建筑,可能与祭祀有关。这一发现为认识琅琊早期历史,以及探讨秦汉皇帝东巡琅琊的文化根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在山东半岛先后巡幸芝罘、成山、琅琊等地,祭祀“八主”神祇,将滨海地区地域性信仰升格,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为秦代国家祭祀加入了新鲜的东方海洋文化因素。这一体系也被西汉王朝所继承,汉武帝亦曾“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信仰的融合巩固了王朝统治,也充分体现了秦汉时期思想文化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的特点。
“楼船入海”:深入海洋的早期探索。随着地理知识和航海经验的不断积累,秦汉时期的人们已不再将大海视为不可逾越的地理屏障。统治者以求仙为目的,主动对海洋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探索,民间也积极向海洋探求更多可利用的生存空间。
据史书记载,琅琊作为重要港口经常是入海航行的出发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琅琊遣齐人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琅琊“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其航线“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又“至之罘”。汉武帝也多次“东至海上”“乃益发船”入海求仙。战国晚期以来,沿海民众为避乱或谋生也多有“浮海东奔”远航者。无论是燕齐方士对于海中神仙世界的描绘,还是秦皇汉武入海求仙的举动,抑或民间的出海航行,均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先民积极深入海洋、探索海洋的文化心理,其催发的航海实践极大推动了他们对海洋认知的进步和海洋文化意识形态的构建。
琅琊台遗址不仅是秦汉王朝统治海疆的政治地标,更是中国早期海洋文明蓬勃发展的重要标识。它犹如一部镌刻在海岸线上的文明密码,揭示了秦汉王朝通过积极有为的措施,实现了从“陆地本位”向“海陆兼重”的转型。
(作者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琅琊台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邱梦颖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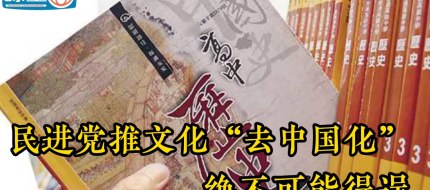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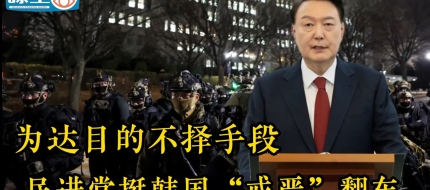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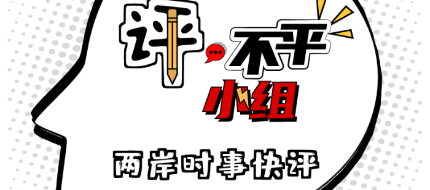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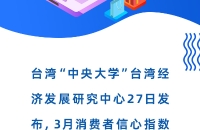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