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思密索心与理会 ——郭守敬的科学精神
郭守敬(1231—1316年)是元朝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历法、数学、水利、仪器制造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通过考察郭守敬的生平经历可以发现,科学精神是推动他的科学研究与实践不断突破的核心动力,也是支撑其学术成就持续发展的内在源泉。
科学精神的形成与构建。郭守敬科学精神的形成与思想体系的构建,既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土壤,也得益于其独特的人生轨迹。儒家伦理的浸润与科学实践的融合,塑造了这位科学巨匠“家国一体”的学术品格与治世情怀。
在邢襄大地的文化滋养中,郭守敬的学术根基始于家学传承与紫金山学派的淬炼。其祖父郭荣精于算数、水利的启蒙教育,与刘秉忠、张文谦等师友以人为本的治学理念相融合。郭守敬在邢州治水时的初试锋芒,不仅展现其“观天察地”的实证能力,更践行了元好问“择可劳而劳,因所利而利”的治世哲学。这种早期实践将儒家伦理具象化为家国情怀的行动准则,为其毕生追求确立了价值坐标。
在宁夏平原的渠系改造中,郭守敬创造性地提出“因旧谋新”的治理范式:通过系统考察唐徕、汉延古渠的现状,采用“旧渠为体,新技为用”的改良策略——保留原有渠网以“节用”民力,辅以滚水坝、调控闸等技术创新,仅用半年时间便重构河套水利体系。这种“传承中创新”的智慧在他主持的通惠河工程中更臻完善: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与漕运压力,他首创“预案先行—分步实施”的工程模式,先以精密勘测建立数学模型,再通过砖石闸技术突破木闸局限,历经20载终成“舳舻蔽水”之盛景。两大工程遥相呼应,彰显其“实证为本”的科学精神与“民本为要”的价值追求。
郭守敬的工程哲学始终贯穿辩证统一的技术伦理。在方法论层面,“节用”原则体现为对既有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邢州石桥修复中的就地取材、渠系改造中的旧基利用、通惠河工程中的木闸革新,无不渗透着成本控制与技术创新相平衡的智慧。在价值维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利国爱民”的济世情怀互为表里:从精确到寸的河道勘测,到以“昼夜通航”为目标的闸门设计,技术细节的极致追求始终服务于改善民生、巩固国本的终极目标,使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超越了工具理性层面。
科学创新与理论突破。郭守敬的科学成就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前人在对他的科学精神进行分析时,都认为“因旧谋新”“继承与创新”是他开展科技活动的前提,是他科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但对郭守敬“因旧谋新”理念的研究多止步于经验层面,事实上,这一思想蕴含着从工匠思维向科学思维的范式跃迁。在改良天文仪器过程中,郭守敬发现水利工程“因旧谋新”方法论与天文、数学的认知共通性。以郭守敬改进创新的简仪为例,它是在传统浑仪的基础上集合“简仪”“候极仪”“立运仪”三者的优势,简化创新而成的新型天文观测仪器。既保持中国传统观测体系,又吸收阿拉伯象限仪技术,制成观测精度达1/12度的仰仪。这种“形器承古,数理维新”的创造路径,呈现了中国传统科学研究理念的创新发展。
在数学方法革新中,郭守敬以实证精神突破传统桎梏。郭守敬关注到“时差”问题。他借助元朝广阔疆域的地理优势,组织了“四海测验”,选取了南北27个测验点,着力解决各地“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问题。通过组织横跨27个观测点的“四海测验”,其纬度测量平均误差仅0.2°—0.35°,其中两处与现代测绘值完全吻合。这种以实测数据将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熔铸为有机整体的有效实践,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达到方法论自觉的新高度,标志着中国传统历法进入实证科学新阶段。在这一时期,郭守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他认为:“前代诸人为法略备。苟能精思密索,心与理会;则前人述作之外,未必无所增益。”
在批判中继承的思维是从历史发展角度对古今、新旧关系的整体把握,已然体现了科学精神。《授时历》工作的具体开展是从天文仪器的改良和数学方法入手的。在对数学方法的整理和应用上,郭守敬的科学思维也体现了其科学精神。在编制《授时历》时,他发现上元积年法不仅繁琐,而且后人往往进行人为附会更改,力求在直觉上达到“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连珠然”的效果。郭守敬认为“后人厌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断截其数而增损日法,以为得改宪之术,此历代积年日法所以不能相同者也”。郭守敬循着怀疑求证的科学路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打破了上元积年法作为“学术公论”的形象,以更为便捷、简要的实测历元法作为替换,从此结束了推求上元积年的历元制度,这是我国历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郭守敬在《授时历》编纂中形成的“精思密索,心与理会”方法论,构建了独特的科研理念。他既肯定“前代诸人为法略备”的知识积累价值,更强调通过“思与理合”实现认知突破。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思维方式既避免了泥古不化的保守倾向,又克服了空谈创新的虚妄之弊。其价值不仅在于具体科技成果,更在于构建了“继承—批判—创新”的科学发展路径。
从“术”到“道”的传承。我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认识论特征强调直观体悟,知识的存在形态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前者能够用语言文字明确加以表达,后者往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必须靠领悟才能把握。在元代理学空谈性理之学的风气下,郭守敬的人格具有独特性。他受传统儒家人文理性精神影响,又结合其科学实践,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体悟与模仿”“实践与调整”“会通与创新”的不同特点,形成了他将儒家“志于道,据于德”的人文理性转化为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以契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宏远的爱国、爱民、敬天、忠君等价值观。
与郭守敬合作共同编制《授时历》的王恂、许衡等人也都从小接受儒家教育,郭守敬的得力弟子齐履谦更是“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下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淹贯,尤精经籍”。郭守敬的后人郭伯玉、郭贵都以天文、历算造福于世,他们的家学传承也都呈现出“技术性”与“伦理道德规范”融合的特点。中国古代科技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是使科技成果变为各种具体的“术”,而郭守敬尤为重视家学中“术”与“道”的传承。
郭守敬的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内核、以现实需求为动力、以实证方法为路径、以继承中创新为思维原则、以民生改善为价值旨归的有机整体。他“因旧谋新”的革新思维、“实测求真”的治学态度、“利国利民”的价值取向,构成中国传统科学精神的典范,其中蕴含的实践品格与创新意识为后来的科学传承发展提供了可供学习的经验。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邱梦颖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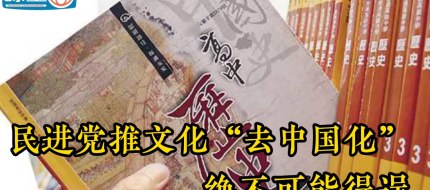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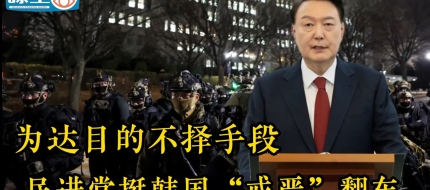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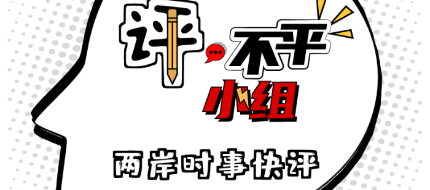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