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叙事激活中国运河的文化记忆 ——电视剧《北上》创作谈
缘于二十年运河梦旅
我出生于江苏,幼年生活在长江边,也算是依水而生的人。犹记得,小时候随父母去看运河,河道不宽,岸边多是堤坝和农田,四周杂草树木丛生,河道上却跑满了货船,一条条首尾相连,一眼望不到尽头。自此,运河便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悄然种下眷念的种子,魂牵梦绕。2014年,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我便一直希望,有一天能用我最熟悉的影像方式,去呈现故乡的运河,让更多的人领略它的独特魅力。
2018年,我读到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仿佛遇见了命中注定的创作契机。这部以京杭大运河为母题的作品,既有百年时空的纵深,又有个体命运的沉浮,将运河与文明的共生关系娓娓道来,深深打动了我。徐则臣笔下那条“流淌着中国人集体记忆”的运河,与我心中那条承载着童年与乡愁的河流,在那一刻重叠了。我与徐则臣的第一次对话,是在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两小时的畅谈,我们达成了共识:运河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文化的血脉,我们在改编中要展现的,是运河人与运河解不开的情缘。
然而,将这部结构独特、意蕴深邃的小说搬上荧幕,绝非易事。原著以意大利人小波罗前往中国寻找弟弟马福德为线索,串起清末、抗战、当代三个时空,文学性与思辨性极强。在影视化的呈现上,我们需要剥开文字,看到文字里更凝练的精神内核、更具象的人物情感。为此,我和编剧赵冬苓老师拉上徐则臣,共同组建了“运河采风团”,从扬州到淮安,沿着运河踏访半月,追溯岁月足音,探寻沿岸人家。沿运河一路走来,随处所见的是新时代下运河散发的勃勃生机:我们采访开书店的老板、送外卖的小伙,做船运的水上人家;见到大量回乡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注重内心精神的修养,他们的善良、真诚和乐观深深打动了我。这些年轻人让我们感怀,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焕发新生的运河和年轻的生命浑然一体,也正是在与他们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萌生了改编的思路,并最终确立了以“花街小院”为核心的叙事方向——用青春的目光看待历史,让运河的浩瀚与市井的烟火交融,让百年历史通过一群“90后”的成长与回归徐徐展开。
生生不息,熠熠昭彰
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化,是“择取与再创造”的过程。
我选择了以2000年后的运河为故事主线,而花街的构建是改编的关键。这座虚构的江南院落,既是物理空间,更是运河精神的浓缩。我们耗时近三个月,在苏州运河段搭建整条花街实景,从青石板路到晾衣绳的剪影,从清晨的油墩子香气到傍晚的炊烟,每一处细节都力求还原运河人家的生活肌理。在第一集中,童年夏凤华领着初来乍到的马思艺穿行花街小院,4分13秒的长镜头串联起小院中五户人家、十五个人的日常。这也是运河“生命力”的视觉隐喻——每户人家相邻而居却活出了迥然不同的生命色彩。
故事的脉络是这样的:2000年前后,小院人家靠水而生,运河的繁荣滋养了沿岸家家户户,所有人安居乐业、欢喜富足。然而,时代浪潮袭来,京沪高速公路的开通使运河航运式微,也深刻影响了运河人家的命运。2007年,孩子们高考在即,在困顿中,他们逐渐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因而向往北上寻找出路。在青春的烦恼、生离死别的考验里,他们历经无数个失眠的夜晚,终于如愿却不那么如意地离开了家乡。大城市的汲汲营营令人疲惫,而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为他们的人生打开了新的篇章。运河应势重生,在北京积累了丰富人生经验的五位青年,鼓起勇气重返家乡,将在故土上、运河边重启一番作为。
在影像呈现上,我将水元素贯穿始终,紧密交织着人物的命运与情感。童年时,他们在运河里摸鱼嬉戏,水是他们的乐园;青春期,他们沿运河北上求学、闯荡,水成为离乡的航道;成年后,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唤醒了他们的根脉,水又化作归乡的纽带。运河就像他们生命的足迹,这种“出走—回归”的循环,正是运河“生生不息”、运河人乐观向上的精神写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生活如何困顿,这群普通人始终抱持着积极的希望。这份坚韧向阳的信念,如暗夜行舟的桅灯,引领他们穿越风浪交加的航运寒冬。潮起潮落间,平凡的坚守酿成星辰般璀璨的人间温情,照亮了彼此的生活,也照亮了运河悠悠流淌的时光。
兼容并蓄,同舟共济
剧中还有一条同样重要的故事线——寻根。
2008年的夏天,一条沉船从淤泥中被发现,几个家庭的过往因沉船的考证被逐渐揭开。抽丝剥茧,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家族的传奇,追根溯源,终将找到个人与运河的关系。一面是马思艺回到意大利探寻自己的身世,一面是陈睿带领着花街“名流”追溯小院各家的过往。最终我们会看到两条线从分开到耦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映照了原著《北上》中动人的兄弟情谊:1901年,小波罗带着弟弟的信来到中国寻亲,一百多年后,小波罗船上谢、邵、周、夏四家人的后人和马福德的后人,在花街小院中重聚。冥冥之中,是运河水指引了他们。一对生前再没相见的兄弟,跨越时空,再次成为了一家人。运河文化的包容性,从地域的融合、代际的传承、情感的共生三个层面展现出来。
剧中的花街是运河船只汇聚的码头,这里有天南地北迁徙而来的人群。剧中马奶奶的炸油墩子、周宴临的长鱼面、刘玉玲的绿豆糕、李燕的豆花,这些饮食细节不仅是生活本真的呈现,也暗含着由运河串联起来的“南米北面”的地域文化交融。从代际上,谢望和的太爷爷曾是翻译,父辈成为运河上的船工,而他自己,则投身互联网行业加入创业大军。几代人的身份转变,折射出运河从运输动脉到文化符号的变迁。故事的最后,花街面临改造,花街小院的五家人不得不迁出,他们却坚定地选择了到新的地方也要住在一起。马思艺初到花街时,六户人家轮流照顾她;马家陷入经济困境时,邻居们默默凑钱相助;谢家陷入伤人风波时,所有人全力支援。剧中展现的是一个小小的院落,但以小见大,从花街邻里间“非血缘的亲情”,映射的是运河带来的情感包容,这种互助并非刻意煽情,而是运河文化中同舟共济的本能。
以影像长卷致敬运河
《北上》的创作历时近七年,从文本孵化到拍摄完成,每一步都如运河行船,需逆流而上的勇气,亦需顺流而下的智慧。对我而言,这部电视剧不仅是对故乡江苏的回望,更是对中华文明韧性的致敬。
运河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在流动中孕育新生;运河的包容性,在于它从未拒绝任何支流的汇入。当剧中夏凤华回到花街的桥上眺望运河,当谢望和带着互联网思维回归花街,我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成长,更是一个民族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自省与超越。
《北上》是一部娓娓道来、需要沉下心慢慢感受的剧作,它的故事有如运河之水不急不缓、自在流淌。静水流深,如果你将剧中那一个个人物当作了自己的同伴、家人,和他们共命运、同欢喜,便能从中收获真挚的笑与泪,为他们的善良赤忱感慨和兴叹。看着剧中的角色一天天长大,我们带着对每个人物的爱,为他们写下了苦尽甘来的圆满结局,这也是我们对现实里所有勤劳善良的人的美好祝愿。也希望《北上》能如运河水一般,润泽观众的心灵,让更多人听见这条河流的低语——它讲述的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未来的可能。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邱梦颖
责任编辑:邱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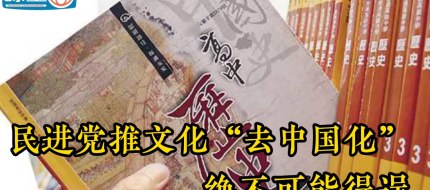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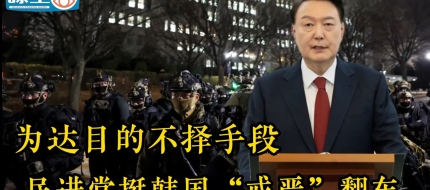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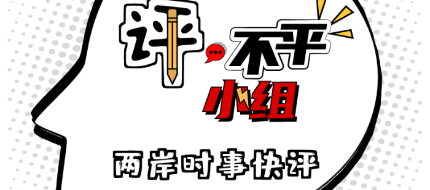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